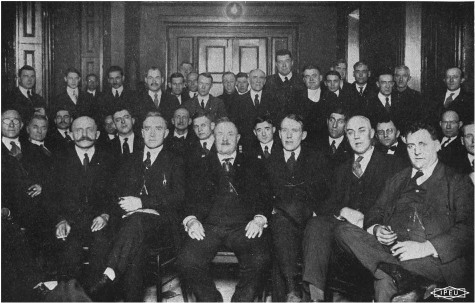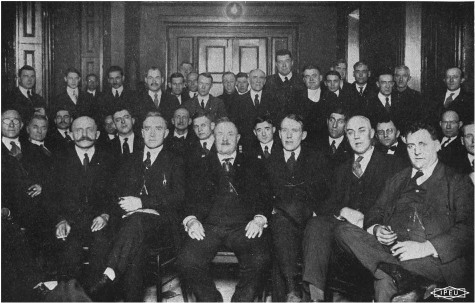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福斯特 -> 钢铁大罢工及其教训(1920)
十三.过去的错误与未来的问题
工人缺乏信心——不足之处——需要与矿工及铁路工人结盟——罢工的激进领导——制造业革命——铁路检修车间工人、波士顿警察、矿工、调车场和铁道工段工人的罢工——联合协会开了小差
在前面的章节中,我已经提到许多钢铁公司及其仆从——市长、议员、警察、枪手、治安队、参议院委员会等——对钢铁工人施加的不义。但要说在前头,我并不把罢工的失败归于这些因素。我把责任放在工人组织的肩上。不管钢铁托拉斯怎样阻挠,只要工会肯稍微动一动,钢铁工人就能赢得这场战斗。
我这样说,不是要提出严厉的指责。相反,我第一个断言,工会在运动中付出了值得称赞的努力,远超它曾为钢铁业做的任何一件事。这标志着工会在战术上的巨大进步。但这还不够,工会只把一小部分力量投入了战斗。钢铁业的组织工作本应是整个工人运动的首要任务。不幸的是,“工运界”的大人物未能充分认识到它的极端重要性,没有坚定地坐在全国委员会的会议上,也没有给予这场运动足够的道义和资金支持,而这些支持决定着运动的成败。工会的悲观主义好比悬在头顶的剑,影响了运动的每一阶段。这源于钢铁业三十年之久的失败。
从一开始,这种悲观和缺乏信心就沉痛打击了运动,后果可以说是致命的。按照运动的原计划(见第三章),本应一开始就把大批组织者投入战场,逼钢铁公司就范,而这本来是轻而易举的。结果,工会犯了大错,修改了计划,付出了沉痛代价。在漫长而艰苦的组织运动和大罢工中,虽然组织者们尽了最大努力,仍无法克服这一错误的后果。这一失去的机会,必然让钢铁业的组织运动付出代价。
整场运动中,酿成这一致命错误的悲观态度俯拾皆是。它绑住了全国委员会的手脚,简直扼杀了一切成功的机会。也许当代没有哪一场大型的工会组织运动和罢工,是靠着如此微薄的资金进行的。考虑到参与者之众、镇压之凶残、运动持续时间之长(十八个月),前一章指出的总支出1,005,007.72美元简直低得可怜。这相当于说,每位工人只拿到4.02美元,换句话说,每人只拿不到半周的标准罢工补助。与其他产业斗争的开销相比,几乎微不足道。比方说,1913年9月23日至1914年12月10日的科罗拉多煤矿工人大罢工中,据信矿工工会花费了近五百万美元,约一万两千名罢工者,每人平均四百美元左右。而在当时,一美元的购买力是钢铁罢工时期的两倍。要是钢铁工人能有这些钱的零头,能打一场无与伦比的漂亮仗。
全国委员会下属工会至少有两百万会员。即使拿出开展组织运动和罢工所需的全部资金,也不算什么了不得的压力。但他们没掏这笔钱,甚至压根没出多少钱。前一章提到,整个工人运动都捐了钱,钢铁工人也交了不少会费。考虑到各家工会的情况,把运动看作一个整体的话,它其实是自给自足的。下一场运动中,以上情况必须改变。工会必须把钱投入战斗,才可能取得胜利。
当我说钢铁工人运动的人力财力奇缺时,当然也包括各国际工会派出的组织者,因为我们能调用的组织者人数还不够满足一半的需求。全国委员会往往求爷爷告奶奶好几周才能要到一个人,把他派到地方上去,把早已登记入会的会员组织到一家分会中。数以百计的分会缺少帮手,许多分会因此直接垮了。有时,就因为派不出人,整片地区都无人问津,这给最终的罢工造成了严重恶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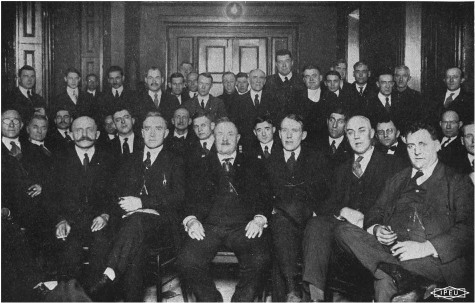
组织者合影
另外,许多工会调动组织者的方式是错误的。工会上级随意使唤人,或者不考虑运动的整体需要,擅自把人调离岗位。这让组织力量变得散漫、无纪律,效率很低。这是不容争辩的。下一场运动中,可以采用两种方式:(一)国际工会明确委派一定数量的组织者参加运动,把他们完全置于全国委员会的指导下。这是劳联、矿工、铁路检修工采取的方式。这种办法行之有效,可建立一支团结的便于管理的高效组织力量。(二)国际工会给工人运动派出的组织者可以结成团队,每个团队由一人主持,负责专门工种。矿工、冶炼工人、机械操作工、电工一定程度上采取了这一方式。一些这样的团队纵向对各工种开展活动,而全国委员会横向对整个产业进行组织工作,就能极大加强整个运动。当罢工来临时,它将不仅是一场产业罢工,同时也是二十四个工种的罢工。这两种方式中,可能第一种更好,但鉴于个人主义盛行,第二种可能更实用些。不管何种方式,都比两眼一抹黑的工会上级遥控底下的组织者要好得多。
不仅是人力和物力,钢铁工人的伟大战斗还缺少兄弟行业的团结。只有钢铁工人自己组织起来,无法与钢铁托拉斯的庞大势力打得有来有回,因为托拉斯还有强大的资本主义组织背书。就像加里有自己人撑腰一样,我们也需要有组织的工人同志出手相助。只有把罢工扩大到钢铁业的界桩之外,钢铁工人才能得到足够的支持。
当工会结束目前的教育运动,发起下一场钢铁工人的组织运动时(应该是在一两年内),应当未雨绸缪:老板更顽固地串通起来反对工人,而工人要更加顽强地联合起来对付老板。到那时,二十四家工会应当同矿工及铁路工人结盟,一旦发生罢工,两位强大的盟友会帮忙釜底抽薪——拿下燃料和铁路运输,彻底瘫痪钢铁业。在1919年11月和12月的煤矿工人大罢工期间,还有1920年4月的“非法”铁路罢工期间,钢铁厂都成片关门了,足以说明阶级兄弟出手助拳的威力。若是钢铁工人、矿工、铁路工人如此这般地联合起来,钢铁公司(或公众)就有可能好好考虑钢铁工人奋战保卫战的那些权利。然后,加里先生也许会意识到,这里不是沙皇俄国,他老人家厂里的工人必须得到人权。
矿工和铁路工人出手相助,也是在帮自己,任何有心的工会会员都不否认这一点。且不说工会会员有义务帮助落难的兄弟,矿工和铁路工人本来就有充分的理由帮助钢铁工人组织起来。美国钢铁公司和所谓“独立”钢铁厂是美国产业专制的堡垒。工人运动中的每一家工会都吃过它们的苦头,托它们的福,忍受着更低的工资、更长的工时,争取组织权的斗争也因此更为艰辛。只要钢铁业的工厂尚未竖起工会的旗帜,没有一家工会能置身事外。不用说,钢铁工人的组织也必然大大有益于矿工和铁路工人。矿工和铁路工人定要不吝相助。这也是他们自己的斗争。
矿工、铁路工人与钢铁工人的联合,并不意味着工会运动从头再来。这只是工人运动不断演变的结果。就这两个行业来说,矿工一个接一个地区挨个儿搞罢工、搞谈判,不过才是几年前的事。就算某地罢工了,别的地方照样干活。铁路工人也一样,就靠单个工种或单个铁路网在搞罢工、搞谈判。他们都觉得跟老板斗的是自己,不干别人的事。这几年是彻头彻尾手工业式的行会主义、特殊主义的全盛时期。谁不拿这一套招数当宝贝,就是别人眼里的呆子。时至今日,两大工人群体正在迅速摆脱上述幼稚的做法。如今,矿工在全国各地同时罢工,铁路工人之间也到处串联,加利福尼亚州圣地亚哥的工段工人可以与缅因州的火车司机并肩战斗。起码可以说,人们已经对老一套很是猜疑了。
在最近的钢铁罢工中,全国委员会曾与矿工和铁路兄弟会安排过一场联席会议,请他们为钢铁工人提供一些援助,哪怕道义上的也好,但无疾而终。在下一场运动中,这些强大的组织应当与钢铁工人结盟,必要时积极施以援手。为此,我们要把运动统筹好,避免招惹法律麻烦,也不要与现有协议起冲突。不过,只需一点主动性和远见,工人就能轻易克服种种技术困难。
庞大的老板利益集团一贯反对任何形式的工人组织与活动。为掩盖这一态度,从而不让工人察觉失败的真正原因——工人力量不足,老板们在全国散播谣言:领头的太能闹腾了,让钢铁罢工搞不下去了;没有约翰·菲茨帕特里克和威廉·福斯特一类的“危险”人物,罢工本来可以顺顺当当的。老板特意点了我的名,说福斯特背地里施展了无数“鬼魅伎俩”操纵罢工。不知为何,工人群众,尤其是支持钢铁运动的工人群众,对老板的嘶吼咒骂不理不睬。如今,工人们越来越乐得让敌人出来宣布谁该当、谁不该当工人运动的干部。臭名远扬的利益集团,就像钢铁托拉斯,越是诋毁某人,工人越觉得这老兄是讲公道的。
如果大家认为我损害了运动,我愿意辞去全国委员会的职务。我不会推脱责任——据我所知,约翰·菲茨帕特里克也是这个态度——但一切如旧。我在1月31日辞去书记兼司库一职,完全出于个人的意愿。
罢工前几个月,谩骂和人身攻击就开始了。当时匹兹堡的一家工贼报纸(靠中伤罢工和工会活动家为生)发表了一些文章,引用了“赤色书籍”以及后来被大肆报道的内容。报上说,革命就在眼前。文章发表后,我立即向二十四家工会的主席发送了副本,他们都回了信,建议我不要理睬,该干什么继续干就是了。看样子,他们觉得受到报纸的猛烈抨击反倒是一种恭维。同样,(在那次诽谤后很久)当龚帕斯主席致信加里要求会面时,我表示自己可能太招摇了,可能引来多余的火力打击,提出辞去负责钢铁罢工全部谈判的会议委员会职务。但我的提议被否决,只好继续留在委员会。另外,运动的任何时刻,只要劳联执委会的干部一声令下,我就得下台走人。这一点,他们在罢工前几个月就知道了。以上种种表明,运动是按照工会原则进行的,劳联内部对此也没有异议。再考虑到钢铁托拉斯的斑斑劣迹,不用说,如果当时没有这般中伤,它们也会使出别的,甚至更龌龊的伎俩。当然了,它们总有手段抹黑这场运动。
过去一年间,对工人的每一个大动作,老板都怀着前所未有的怒火来对抗,政府官员亦然。这一点坚定了我的上述想法。在整个欧战期间,看到工会猛进的势头,权贵们毫不掩饰惊恐和仇恨,却无力阻止。但现在,他们可以肆意报复了。当前的白色恐怖时期,他们总用老一套:先把罢工污名化、质疑罢工目标的合法性,让腐臭不堪的新闻界挑拨群众反对罢工,再不择手段地粉碎罢工。无论运动多么温和又平平无奇,总有办法鸡蛋里挑骨头,大肆搬弄是非。
首当其冲的是铁路车间检修工人。先是铁路管理局把铁路工人的诉求拖了几个月,收入微薄的铁路工人在百物腾贵的刺激下,终于在1919年初夏发起了一场自发罢工[1],结果被彻底打垮。了解情况的官员说,一度有二十多万人参加了罢工。自然,报纸把这些工人斥为布尔什维克。在得到“提高待遇”的承诺后,工人复工了。最后威尔逊总统下场,宣布提高工资有悖于政府降低生活成本的政策,提请暂时搁置工人的要求。国家首脑的声明等于给了反动势力一把尚方宝剑,干脆瓦解了各地的铁路工人运动。工人的努力大为受挫。到1920年5月为止,工人的生活毫无起色。
接着是1919年9月的波士顿警察罢工事件。罢工的起因是向来保守的警察试图组织工会。大公司豢养的州政客蓄意打压罢工,无情解雇了新生工会的一大批干部,坚决不让他们复职。当罢工不可避免地发生时,不仅被贴上了“闹革命”的标签,还被说成“动摇了文明的根基”。剩下的事就归新闻界操办了。罢工被淹没在无数的谩骂、歪曲、诋毁之下。
1919年11月又轮到了煤矿工人。大战中,六万矿工来到法国前线。这些矿工买下了数不清的自由公债,埋头苦干,保持产业运转。矿工觉得自己在战争中赢得了一些自由,但当矿工要求这点自由时,发现除了罢工别无他法。保守老派的矿工工会领袖都被痛骂成革命家。参议员波默林[2]说[3]:
多年前,有位范德比尔特说“去他奶奶的公众”,吓了美国精神一跳。但这话不是他的专利,就算是他的独创,如今也受到了挑战,因为有人比他还漠视公众福祉。某位福斯特比起他来毫不逊色,此人靠着国内的极端社会主义者和产盟分子撑腰,企图把全国的钢铁工人都招入麾下,还想叫产业瘫痪。还有某位刘易斯(美国矿工联合会主席),为了自己的野心,在同一伙人的帮助下,号召四十万人离开矿井,对公众说:“要么冻死,要么挨饿。”
政府指责罢工“不合理又不合法”,援引“莱沃法案”对付罢工。这项法案原本是打击战时粮食与油料投机的,在法案通过时,发起人众议员莱沃[4]与司法部长格里高利[5]明确表示,它不适用于为改善条件而罢工的工人[6]。战争结束后,至少对老板来说,法案已经失效。但官方正是以这项法案为依据,宣布矿工罢工非法的。联邦法官安德森发布禁令,勒令工会干部撤回罢工指示,不许给罢工者提供任何道义或经济支持。情况糟得不能再糟了。多亏矿工出色的组织和煤炭业的战略地位,矿工们才免于惨败。11月11日,在工会干部点头结束罢工后,《费城公报》表达了一个普遍的看法:
其实,我们在煤炭问题上都“弄错了”。可以坦白说,政府在处理局面时,用上了德国战时总督以军靴驯服比利时小镇的策略、“灵活性”与“和解精神”。
然后是调车场与铁道工段的工人自发罢工。物价不断的涨,工资纹丝不动,显然工人忍无可忍了。为了击败罢工,资方又把“莱沃法案”从坟墓里刨了出来,拿它监禁罢工领导人。但还没完。我国大概还没有过一场大罢工是这么自发和无计划的。但我们的司法部对此毫不费心:它刚刚向轻信的世界宣布,整件事是颠覆分子精心策划的阴谋。写到这段时(4月15日),我在报上读到,司法部长帕尔默把我列为了罢工领袖。报上用了“帕尔默指责福斯特教唆铁路罢工”之类的头条[7]。
在帕尔默先生的“廉价惊险小说”基础上,当地报纸添油加醋。例如,《匹兹堡领袖报》事无巨细地报道,我几天前是如何乔装打扮,从西部回到匹兹堡的——想必是在与帕尔默先生口中了不得的“革命者”搞了一出密谋之旅以后。这些“革命者”不仅挥挥手就让整个产业停下,而且是在成千上万工人都“知情”,而直到罢工前夜,司法部仍蒙在鼓里“不知情”的情况下,办到这一点的。
说真的,我一直忙着写这本书,几周都没出家门。自从钢铁罢工结束后,我就没离开匹兹堡附近。另外,我不认识任何一个报上所说的“罢工领袖”,也没和这些人有联系。我没参加过任何一场罢工会议,也没当面见过任何一位罢工者。司法部和报纸才不管这些。报上更是放肆表示,希望帕尔默的指控能把这些人赶回去干活[8]。这才是他们的目标。这些指控跟事实不沾边,纯粹就是为了击败罢工[9]。
类似的例子数不胜数,说明以往的斗争中,工人受的攻击有多么阴险——新闻把西雅图和温伯尼的总罢工罗织成“革命”;不久前,龚帕斯宣布劳联要继续“奖赏朋友,惩罚敌人”的一贯政策时,也惨遭指控为企图占领政府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到这里打住吧。钢铁罢工直指美国产业专制的心脏,必然遇到最顽强、最疯狂的抵抗。如果有权有势者没指控罢工的背后有“赤色分子的鬼魅伎俩”,大可放心吧,总会有不相上下的指控。下一场运动必须靠自己的力量获胜,而不是靠报纸制造的反复无常的公众舆论。
但是,比上述全部问题迫切得多的,是钢铁锡工人联合协会对运动的态度。罢工结束后,联合协会立即退出了全国委员会,至少目前是放弃组织巨型钢铁工厂了。因此,整个运动危在旦夕,因为联合协会掌控着近半的钢铁厂工人,包括具有战略意义的炼钢工种。没有它的支持,其余人不可能取胜。除非联合协会归队,否则钢铁业的联合行动肯定会打破,结果只会让加里先生一伙人乐开花。
钢铁锡工人联合协会的消极态度,与协会多名干部在本次罢工的立场是一脉相承的。从一开始,他们就给运动泼凉水,常常挑毛病,不肯配合。正如第六章所述,联合协会公然当着运动的面,想跟美国钢铁公司和解。至少,他们给钱都十分吝惜[10]。罢工中曾有几周,当胜利逼近时,联合协会的表现稍微有了点热乎气,很快又冰凉了。联合协会采取了“及时止损”的政策,罢工结束好几周前,就急于取消罢工,还四处劝工人复工。更糟糕的是,联合协会曾试图与钢铁公司单独媾和。罢工不到两个月,他们就在斯帕罗斯角向伯利恒钢铁公司提出以下协议(结果惨遭回绝):
1919年11月19日
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的伯利恒钢铁公司与员工签订如下协议,规定炼钢部门的工资待遇。
一.双方同意,西部钢铁与洋铁生产商和钢铁锡工人联合协会于1919年6月的大西洋城会议上商定的工资待遇,将由伯利恒钢铁公司接受。
二.公司同意让前员工复职,且就业不受歧视。
三.上述协议将于1920年6月30日到期
罢工期间,联合协会的干部不厌其烦地重复自己是如何珍视跟老板签的合同,而且不惜损害罢工,也要毫不迟疑地坚决“履行”合同。但轮到自己向别的工人履行义务时,情况就不一样了。他们很清楚,跟美国钢铁公司与伯利恒公司私下媾和,已经违反了自己与钢铁业其它工种的庄严誓约,更不用说违背了工人团结的基本原则。
眼看其它工会在自己一家独大的产业里成长起来,这些干部毫不掩饰酸溜溜的心情。他们在全国委员会里玩弄手腕,不止一人热衷于给委员会使绊子。看他们的表现,不像是希望钢铁业组织起来。不说别人,我的好一部分时间都在给他们擦屁股。显然,他们总能得到某些同僚的衷心支持。不过,公平地讲,联合协会的基层干部和群众都强烈支持全国委员会的运动,提供了忠诚的合作。
至于联合协会退出统一行动的理由,钢铁业有传言说,它今后要吸纳更多的成员,成为一个真正的产业工会,庇护钢铁业上上下下的工人。但熟悉钢铁协会的人都不拿这话当真。联合协会是一个根深蒂固的技术工人工会,四十五年前成立以来,便是如此。它诞生于“吨位工人”,即制钢和轧钢的技术工种。它的每一样习俗、政策、本能,都产生于这一类工人的群体利益。过去几年里,联合协会始终声称机械性工种和普通工人受自己管辖,可从未关注过这些人的福利。在联合协会存在的工厂里,往往只有“吨位工人”享受到协议,其他工人都被置之不理。的确,在这场运动中,在全国委员会的推动下,工人都被联合协会纳入了协议,但联合协会总是不情不愿的(第十章就是一例典型)。
事到如今,说联合协会的领袖要放弃这些手工业式的做法,把组织革新成一个充满活力的真正产业工会——这对见识过他们手法的人来说,是难以想象的。可就算奇迹发生了,他们摆脱了十九世纪中叶的思想和方法,采用了现代的原则与制度,开展了组织钢铁业所必须的全面运动,也解决不了问题。钢铁业的其它工会不会向联合协会让步,更可能为争夺会员闹得不可开交。如此一来,组织起钢铁业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工会必然只顾内斗,没有时间、精力,乃至雄心壮志,再次投入与钢铁托拉斯的新一轮交锋。
要推动钢铁业的进步与组织,就不能分裂队伍和分散力量,而是巩固和扩大它们。钢铁业各工种团结一致,与矿工和铁路工人结盟,一旦钢铁工人遇到困难,矿工和铁路工人就能拔刀相助。这是唯一合理的希望。钢铁工人正迅速从失败中缓过来。教育运动[11]也逐步取得成果,这项工作应当常态化,直到全行业组织起来。这时候,联合协会若半途而废,无异于自杀。更糟的是,这是对工人运动的罪行。这会破坏运动,让无助的钢铁工人再次听任加里一伙剥削者的摆布。工人组织不应当允许这种事发生。几个目光短浅的工会干部就能阻挠一个庞大产业组织起来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1] 自发罢工:原文an unauthorized strike,即未经授权的罢工,非法罢工。比如没有经过会员投票或工会官员批准,或法律规定不可罢工的情形。——校对者注
[2] 阿特利·波默林(Atlee Pomerene,1863年12月6日——1937年11月12日),美国政治家。早年参加了民主党。1911年1月9日至3月3日任俄亥俄州副州长。1911—1923年任参议员。——中译者注
[3] 出自1920年2月的《制桶工人报》(The Coopers’ Journal)——原注
[4] 阿斯伯里·弗兰西斯·“弗兰克”·莱沃(Asbury Francis "Frank" Lever,1875年1月5日——1940年4月28日),美国政客。1896年加入民主党。1901年任南卡罗莱纳州众议院议员。1901—1919年任众议院议员,期间于1911—1919年任众议院内务委员会主席。1919—1922年任美国联邦农业贷款委员会委员。1930年因病脱离政治活动。——中译者注
[5] 托马斯·瓦特·格里高利(Thomas Watt Gregory,1861年11月6日——1933年2月26日),美国律师。1892—1896年任得克萨斯州副检察长。1896年起任得克萨斯州法官。此后参加了民主党。1913—1914年任司法部长特别助理。1914—1919年任司法部长,期间参与制定了《间谍和煽动叛乱法案》,起诉了超过两千名反战人士。1933年去世。——中译者注
[6] 关于重要的细节,见1920年1月《美国工团派》(American Federationist),塞缪尔·龚帕斯的《破碎的誓言》(The Broken Pledge)一文。——原注
[7] 见1920年4月15日《匹兹堡邮报》——原注
[8] 见1920年4月15日《匹兹堡电报记事》——原注
[9] 因为这件事,我称帕尔默为骗子。这段说法被媒体广泛转载。但帕尔默没有接招。在这种情况下,他有两种选择:如果他对我的指控是真实的,按照他对“莱沃法案”的解读,他有责任逮捕我。如果它们不是真的,他照道理要承认,他在媒体上发表的攻击我的言论是错误的。但帕尔默什么都没做。期间,我受到了新闻界的猛烈抨击。例如,宾夕法尼亚州《多诺拉先驱报》于4月16日写道:“威廉·福斯特看来是想闹一场小革命出来。要治好这种病还是得用老式疗法——吊死。”
不难想象,如果在一份工人出版物上刊登这种教唆谋杀的话,司法之轮会转得多快,编辑会多么迅速地被关进监狱。但是,匹兹堡的司法部官员对这段话无动于衷。邮政部门也一样,因为《多诺拉先驱报》是邮寄的。同样,县和州的官员也置之不理。最后只能告它诽谤。但在黑暗的宾夕法尼亚钢铁区的心脏,一名工人对上钢铁托拉斯的同伙能有多少胜算?——原注
[10] 在第六章末尾的报告中,表明联合协会在运动中得到了70,026名会员。但由于上述原因,这个数字是严重低估的。M.F.泰伊主席在向参议院委员会作证时(听证会记录第353页),又给了一个说法,他说书记告诉他“已经发了十五万张会员证”,印都印不过来了。从这支工会大军手上,联合协会总部能从每个人那里收到两美元。而作为回报,联合协会在整场运动中,只交给全国委员会11,881.81美元的经费,其中3,881.81美元用于组织工作,8,000.00美元为罢工者——一半是联合协会的会员——提供食物和法援。联合协会在各方面为罢工提供的帮助都非常少,金库里还结余很多收上来的钱。——原注
[11] 工会教育联盟(The Trade Union Educational League),1920年在威廉·福斯特的领导下在芝加哥成立,旨在推动独立的工人阶级政治行动。1922年起通过美国共产党获得共产国际资助。后期被隶属于劳联的工会边缘化。1929年在共产国际“第三时期”路线的影响下改组为工会团结联盟(The Trade Union Unity League)。——中译者注
上一篇 回目录 下一篇